画奴---------原创小说请勿转载
第一次见到画儿,是在家乡的小城,东北夏天的傍晚竟格外酷热。
还记得那家毗邻郊区的饭店,大幅日历遮遮掩掩着斑驳破旧的墙壁,我和男朋友安排几个刚刚失业的兄弟在这里吃饭。圆桌上的爷们愈喝愈起兴,渐渐脱去上衣,赤裸着肌肉饱满的臂肘搭在对方肩上,一面浮夸地吹嘘着自己,一面对世间万态嗤之以鼻,谈吐间眉飞色舞,真情实意。 我喜欢酒后的男人,在酩酊大醉之后的迷幻状态中,他们心目中的自己是成功的,踌躇满志的,心胸宽广的,重情重意的;而现实状况下那个失败的,困顿窘迫的,狭隘自私的,虚伪无奈的他们会在灵魂中暂眠。
上菜的小服务员似乎有点心不在焉,她一面端着盘子,一面回头关注着店老板的一举一动,由于太消瘦,锁骨拧成一个奇大无比的的结。直到几桌人的菜上的差不多了,她终于鼓起勇气走到老板身边,低声恳求些什么。好像是索要工资,但是老板并不乐意支付,找各种理由搪塞她,两个人不停地讨价还价。我觉得有趣,暗自观察她们。
她执拗地争辩着,丝毫不见气馁,这令我联想到无数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纯良少女,她们对这座森林的险恶一无所知。我决定不再坐视不理,走上前去。如果当时我知道她的真实身份,可能不会有这样冲动的怜悯之心。
“买单!”我招呼老板。
“二十二瓶啤酒,两个有奖的不算。。。一共三百一十六!”老板数着啤酒瓶子。
我拿了十六元给老板。
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你欠她三百工资不是没钱给吗,我帮你给了。”
因为我身后是一桌醉醺醺的男人,所以我说这话的时候理直气壮。在东北这种野蛮的地方,谁也惹不起的就是这样一群亡命之徒。我塞了四百元给她,回身往圆桌走,她却追上来,把多出的一百塞回给我,还抬头看看我。我第一次看清她的眼神,执著坚定,不容置疑。
我们一行人摇摇晃晃地离开饭馆,与此同时她也失去了工作,远远地跟着我们的队伍,不离去也不靠近。男人们还要去KTV走“二场”,我婉拒他们的邀请,送走了所有人之后,我回头看她。漆黑安静的马路上,一个颤抖的小身影,在夜色中显得更加孤独无援,她不料到我要回头,却也来不及躲闪,于是缓缓地,尴尬地挪到我跟前。
你不会懂得,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来说,有多么撩乱人心。“你能带我走么?”她第一次开口对我说话,那一瞬间动人的声音,我已彻底融化,束手就擒。我把她领到自己的公寓,安排她睡在我的床上。
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艳遇,因为我自己也是女人。一夜无眠,我注视着她熟睡的样子。她睡得很沉,精疲力竭,一定是个经受过很多苦难的孩子。
以后的几天她都在我的家里,像一只宠物一样,不劳而获地生活。她没有钥匙,也从不离开我的公寓。她说她叫画儿,我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声声叫着“画儿,画儿”地满屋找躲猫猫的她。我养活她,给她购物杂志让她挑选,任何她喜欢的东西我都会买给她;我给她洗澡,抚摸她雪白的皮肤和棱角分明的蝴蝶骨,那时候虽然没有对她有任何邪念,但是这已经成为让我极其享乐的事情;就连中午我也放心不下,非要从单位回来一趟看看她,买新鲜的水果和零食给她吃。
没有条件的对她好,我心甘情愿,一个女人为了一个女孩而痴迷,我不敢想象,却已深陷不已。
改革春风终于吹到我们单位了,裁员公告贴出来,我们上面已经有六个人员被突然拿掉,此时全集团上下都人心惶惶,草木皆兵。
为了保住这个位子,有好几天的中午忙的没空回家看她,这次我突袭回来,开门时竟听见她仓促收拾东西的声音,我奔回屋里。
她从被窝里翻起来,脸色出奇红润,身上有细密的汗珠,连连喘着粗气,大眼睛惊恐地看我。电脑里播放着我下载的激情片,我掀开被子,她忙缩手回去,却被我抓住,那是一根肉色的振动棒。她竟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玩我的东西!我给了她一个耳光,不是因为她动了我的隐私物,而是因为她破坏了她自己在我心中的纯洁形象,我一直以为她是那么单纯童真,她的身体和心灵都神圣得让我不忍触犯,可她却用这种东西破坏自己。
她低下头捂着脸,几秒钟的沉默之后,她爆发出长长的一声“嗯----”,像小孩子受委屈一般的哭泣声,声音不大,却让我不知所措。我有些后悔,把她抱在怀里,抚摸着她的头发说些安慰的话。
画儿,别哭。你喜欢玩就玩吧,还不行么?但是别用我的,你想要什么我再买给你。
我开始怀疑她是个什么人了,她不但懂得许多新潮的东西,比如网购和名牌,而且对保健品商店里的东西都一清二楚,这绝对不会是个涉世未深的农村丫头所能了解的。
可是更令我苦恼的不是这些,自从那次打过她之后,我竟然有种奇怪的感觉,那是一种生理反应,好像伴随着她的痛苦和哭泣,我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。
那天晚上吃完饭,我给她试验新买回来的振动棒。
这算什么?我不曾设想自己会做出这种事,我们两个人赤裸着身体在床上翻滚,而后我将震动棒插入她湿漉漉的身体。几遍抽出和推进,看她的眼神渐渐变得迷离,我一手从上面按住她的头不让她逃离,一手把整个大家伙抵在她身体最里面。已经到达极点不能再进入,我知道那一端一定深深扎在她的最深处,而她却动弹不得。
她的巅峰是那么真实,不似日本激情片里的那般做作。她全身雪白的肌肉绷紧,不由自主却颇有节奏地颤抖,伴随一声似受惊小兽发出的低吼,她倾泻而出,一股一股的白色溪流泉涌。之后她瘫软下来,嘴角抿起一丝微微笑意而熟睡过去。
谁看到这样的女子不会动心?我想,曾经短暂拥有过她的男人,该是多么满意跟知足。
睡觉的时候画儿喜欢平躺在我怀中,把我的手捂在她的下体上,她说要我这样保护她,梦里她就不会害怕被人欺负了。可我有时候竟像个男人一样毛手毛脚,两跟手指头不听话地往里滑,整宿折腾她让她无法安心睡眠。
两个人这样相依相伴,我已不再需要任何其他人。几次不接男朋友的电话,他开始疑神疑鬼地刺探我,“早听说你们厂长的儿子和你很熟了,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吧?”于是我也不妨对他直说,其实我早开始就没有什么心思和他认真相处,他是一个司机,风餐露宿朝不保夕,而我的条件比他好太多,就算我愿意,我父母也不可能答应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他这种人。况且眼下我只要画儿在身边,我的收入可观,可以自食其力,我愿意照顾她,养育她。
但是画儿始终不是一只真正的宠物,她是人,有自己的家人,有自己的学业和生活。不知为什么,当我问起她时,她却总是沉默不语。
“画儿,你怎么不说话?”
于是她就扑到我怀里,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,弄湿我的文胸,热热的泪水渗入我胸口里,我赶忙给她擦拭,再也不敢深究这个问题。
我们买工具的那家店铺提醒我们尝试一些新奇玩意,有几种钢制的手铐,和真的手铐一样有锁孔和钥匙;还有牛皮鞭子,分为一股和散股的;绳子,铃铛,蜡烛和夹子,还有电击和导尿管。但我最中意的是一条火红色镶嵌着两排金属片的狗链。
画儿,既然你没有家,没有身份,那就做一个真正的宠物吧!
很久以前,我下载过一个“不激情的”激情片,名字好像叫《暗室の饲育》,冗长的五集剧情,无非就是讲孤独老男人抓走年轻女孩当做宠物饲养起来的故事,整个影片只是描述纠结的虐恋——时而蹂躏,时而爱怜。因为缺乏高潮迭起的镜头所以我没有仔细看完,现在回想起来,影片里提到过这种关系应叫做“主奴”。
我和画儿提出我的愿望,她竟一口答应。于是我下功夫好好研究了一下各种工具的用法,借鉴了许多主奴电影,又上专业网站细心参谋游戏规则,才试着和画儿开始第一次。
“跪下。”我命令她。
从什么开始呢?我回想起第一次打她耳光时她那又惊恐又怨恨小模样,至今令我牵肠挂肚。“啪”的一下,我把第一个耳光落在她左脸上。
不知道是力度不够还是她心里明白这是游戏,她没有哭,捂着半张脸蛋伸伸脖子,小心翼翼地抬头看我。
“啪”,第二个耳光稍重些。
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捂,于是我用手铐把她的小手牢牢的固定在身后。她实在太瘦,每次骨头和手铐碰撞都发出哗啦啦的响动。劈里啪啦地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,我听到熟悉的一声“嗯——”,她哭了,这一次我看的很清楚,圆圆的大颗泪珠从她窄小的脸颊滑落,我赶紧抱住她,我觉得自己很变态,既心疼她又这样欺负她。于是我们换些别的项目来玩。
我平躺在床上,让她用胸部给我推拿,说实话她的胸像幼女一样平坦,还不如我自己饱满,好在两颗粉红色的肉钉十足诱人,这样在我身上几番来去,我不禁舒服地发出一声呻吟。她好像得到鼓励似的,伸出舌头在我皮肤上乱划,像一条游走的蛇在我身上快乐地爬行,似痒非痒的触感令人销魂。
在我人生记忆里,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“服侍”过我,他们敷衍了事,执着结果,如果不能如愿以偿,是不会为女人做任何徒劳的事情的。
画儿很乐意做我的奴,满足我践踏她心灵与肉体的愿望,她甚至故意启发我,惹些小祸让我收拾她,有时候我捆绑和鞭打不当给她造成瘀伤和出血的鞭痕,她也摇头说不疼不怪我。这样的奴儿我怎么能不喜爱,也更加怀疑是谁这么狠心,会抛弃她这样一个善良可人的女孩儿。
平时她就带着我买给她的红色狗链在屋里爬来爬去地玩,有时候我看她高高翘着臀部咬玩地上的毛绒玩具,就觉得好笑,她的样子真的活像一只真正的小狗。
我也会偶尔生她的气,那时她就会垂下头乖巧地舔舐我的脚趾,把整个大母脚趾含在口中。我推推她说不要这样,我涂了趾甲油。
对于做奴,我没想到她竟无师自通,而且表现出色。
“女主人!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每次我回家,她都这样呼唤着我,连爬带跑地奔到门口迎接我。
其实,我最愿意看到的,是她身不由己,任人鱼肉的样子。第一次玩暴露,我把她领到楼顶天台的边缘上,扒下她的裤子,让她白白的臀部“俯览”城市风光。我们所住的公寓楼层很高,虽然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么高的楼顶,但是画儿还是提心吊胆,摇头尾巴晃地哀求我。她这样一晃,更加让我兴致大起,于是我命她扒开阴部,让她用两个小洞向对面公园里的哥哥姐姐打招呼。她也真不争气,还没怎么样,便湿成一条小河了。看到她这副狼狈样我也激动起来,我撩起自己的裙子,褪下丝袜和短裤,按着她的头逼她为我吮吸。弄了半天还是发泄不掉,我把她牵回屋里,让她用振动棒服侍我,她的小手笨拙地握着棒子左一下右一下地乱捅,一不小心碰到了无极旋钮,剧烈地震动起来,吓得她把家伙扔到一边。
“你想弄死我啊?你这么喜欢强烈那我就成全你!”我不由分说把她按下去,将振动棒频率调到最大,狠狠地塞入她体内。
“啊!”
受不了这样突如其来的刺激,她大声呻吟起来,两只手惊慌地在空中乱舞。看来我还应该再做点事情,我取了绳子将她两手举起绑在床头,又拿袜子揉成一团塞入她口中。然后继续不管不顾地玩弄她。
是太兴奋或是太疼痛,她被丝袜堵住的小嘴还是发出很大声的“呜呜”浪叫。于是我取出袜子,掐着她鼻子用自己的嘴堵住她的嘴唇,强行将舌头伸入她口中,另一只手继续用振动棒狠命地欺负她。
没多久她真的受不了了,窒息加上肉体的痛苦使她临界崩溃边缘,我看见她的小脸蛋渐渐由红转白,我松开嘴后,她缓了好几口气才渐渐清醒,然后我又吻住她的嘴,让她无法呼吸,这样周而复始,当我最后一次吻住她,她突然睁开紧闭的双眼,呜咽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,但是来不及了,一股粘稠的热浪冲到我手上,她竟然喷泄而出。
也许我真的喜欢女孩,也许我的生命注定有一半是男人的角色。
好不容易又挨到了星期五,我迫不及待地收拾文件想尽早回家见到画儿,刚刚摞起来的文件却被一位女同事莽撞地刮掉在地。我直起身想说没关系,可是没有人对我说对不起,刮掉我东西的那位一股风似的向门口颠去,头都没回。
原来是他来了,厂长的儿子。这帮女人一个个谄媚地粘上去嘘寒问暖,稍有姿色的都没留在座位上。我心中一阵作呕,同样是女人,她们和画儿的差距怎么会那么大,看见她们这幅德行我就清醒地知道我不喜欢女人,只是喜欢画儿罢了。
这位谦谦公子到让她们失望了,他径直走向我,帮我收拾散落一地的文件,然后约我出去吃饭。不知道是不是虚荣心作怪,我答应和他同行。其实早在他父亲没坐上厂长位置之前,我们就已经很熟,我们是同学,又是朋友,但是在这以前集团的人从不知道。如果不是因为刚刚听说我甩掉那个男朋友,他也不会轻易接近我。
看来他一出手,就有了十成的把握。坐在餐厅里我脑筋飞速地转动,因为他已经频频暗示,接受和拒绝只在我一念之间。我想到厂里占满一张板报的巨幅裁员公告,婉拒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。我有什么不能接受的?眼见要三十的我每天醒来都比昨天老一些,父母步步紧逼令我透不过来,难道为了画儿。。。
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,无法为了一段根本没有结果的感情做这么伟大的牺牲。于是我答应他饭后一起去看电影。
等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,画儿不再床上,我心急地打开灯到处寻找,最后在阳台角落里找到她的小身影。时下已近冬,她竟穿着单薄的睡裙在开着窗户的阳台上睡着了。想必是盼望我回来,一晚都在这儿眼巴巴地张望,直到困倦得挺不住才睡过去。
我推推她,她一动不动,再摸她额头竟像是烧开了一样滚烫。我把她背到楼下,打车送到医院。她这次真是惹了大祸,病得很重,需要住院。
打了两个吊瓶之后,她醒过来,看见我,张开口说出沙哑的第一句话,“你上哪去了,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!”
看她咧着嘴就快就快哭出来的样子,我不知如何解释好,在这个时候告诉她我要和别人恋爱结婚,实在说不出口。
当晚医生过来,说最近非法组织活动猖獗,坚持要我们出示证件。我拿出自己的身份证。
“你妹妹的呢?”医生问。
“她,她的没带来。。。”我支支吾吾地解释。
“哦,原来你用自己的名字登记的,这样不行,她叫什么名字?必须用真名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你连你妹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?”
“她不是我妹妹!”
接下来的话不知道应该怎么说,难道告诉医生她是我的女伴,或是我的一只宠物,一个玩具?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,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多么有悖人伦,可耻至极。就在这一瞬间我也下定决心——是时候和她有个了结了!
第二天早上,画儿没醒来,我接到父母的电话,厂长和厂长夫人请我们一家赴宴。能这样闪电般地谈婚论嫁,是我史料未及的,但我倒也的确迫不及待,纠结在那种龌龊的关系中到什么时候才能完结!
晚上回来,画儿已经醒过来,她精神好许多,和临床的大婶有说有笑,嘴里啃着人家分给她的苹果。见我进来,她兴奋地蹦起来,但是手上连着的吊针让她不能上前,于是她就直直站在原地,期待地望着我。
我也不动,就这样远远地打量她,也许以后没有那么多机会好好的看她了。她还穿着那件单薄的睡袍,邋邋遢遢得皱成一团,锁骨已经不那么清晰,脸蛋因为病态的浮肿而显得通红,我才发现来我家的几个月来,她已经圆润了许多。
然后我走上前,轻轻地拥抱她。这个傻丫头到现在还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对她做的事,糊里糊涂的在我怀里傻乐。我说:“画儿,我要走了。”
她吃惊地看着我,然后像是一个被邻家哥哥欺负扒光扔在大街上的小女孩儿一样,双手紧紧抱在胸前蹲下身哭泣起来。
办完出院手续,我带着她在街上转了好几个圈,买了衣服和食物给她,最后还是于心不忍,领她回到家里。我们各自睡在床的两边,我背过去,听见她打开振动棒开关自娱自乐起来,还故意高声呻吟。
我气急了,打开灯,抓出鞭子对她挥去,我使出全身的劲重重地打,下了死手。她尖叫着缩进墙角,只把后背露在外面,藏无可藏。散鞭打断了好几根,我又换一股鞭继续打,她只是痛苦的哀嚎,却绝不求饶。不知道打了多久,我突然意识到她早已不出声了。我停下手,看见她的后背皮开肉绽,一道道淋子在灯光下反射出血红的亮光。 振动棒还插在她轮廓清晰的下体里,发出嗡嗡的响动。
我有点担心,她毕竟大病初愈。我把她翻起来,原来她还清醒着,睁着双眼,头发乱糟糟地铺盖在脸上,面无表情。我把她扶到床上,慢慢取出振动棒,拿了医药箱给她包扎伤口,“这次怕是要留疤了。”我说。
“我知道这不是游戏,你真的讨厌我了,对吧。”她看着我说,我以为她又要哭泣,可这一次她面带笑容,表情轻松又平静,仿佛世间的苦难都已离她远去。我心里觉得不妙,但我不能否认她的话。那一夜我拥着她缠满绷带的身体入眠。
第二天她消失了。最后一次见她,是在两个星期后我的婚礼上。宴客厅外出现一个穿着白色婚纱的女孩儿,那婚纱的剪裁和我身上所穿的像是一对儿,许多人都把她当成我的伴娘,但是那身影只是一闪而过,我还来不及看得清楚,便不见了踪影。也许在画儿心里,她自己就是我的另一半吧。
后来,在报纸上看到新闻,华侨夫妇在国内失去音信一年的女儿突然回到家中,身上伤痕累累,神情呆滞,无法开口说话,怀疑是精神受损,其父母已将她带回国外治疗。接下来的篇幅还言简意赅地描述她此前的经历,早恋,逃学,怀孕,离家出走,被对方抛弃,回家,堕胎,再次离家出走,被追回,再次早恋,离家出走。。。
不足一年,我升了职。我是厂里唯提拔到副科级的女性,其他一起来的女同志被裁员下岗的不在少数。
很多年后我带着儿子走在马路上,看到一个疯了的少女,衣着破烂,对着路人痴痴傻笑。我以为是画儿,想仔细看看,又明白过来,若是画儿还活着,应该是个成年女人了,绝不是这个年纪。
真的疯了有什么不好,她一路且歌且行,对世间的苦痛无知无觉,从此也就不会再受到伤害。也许我是最后一个伤害到她的人了,我看着那个少女自言自语道。但是这种安慰和欺骗自己的话毫无效果,我思念她,想见她,我悔恨当初那么无情地抛弃她。我终于意识到,其实我从未忘记过她。
有关画儿的记忆没有随着时间被吞噬掉,反而与日俱增,在我心里形成一条汹涌放纵的大河。不问来途,不问归处,画儿,我只问你是否能够原谅我的自私。
我多么渴望再次将她踏于脚下,鞭笞她的身体,欣赏她的无助;即便不能,我但求上天给我机会拥她入怀,亲吻她的头发,抚摸她的瘦弱;罢了,我只愿能远远的在人群中捕捉到她的身影,依然是翩跹轻快,笑语盈盈,就知足了;若这也算奢望的话,画儿,我唯有祈求来生再遇见你。来生,让我做你的奴。
关键字: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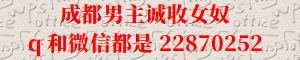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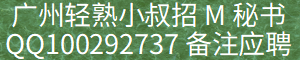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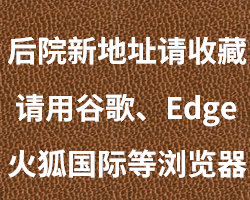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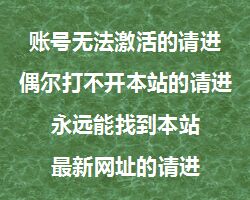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