虐恋在中国“网络风行”,“中国性学专家”李银河女士是“劳苦功高”的。
李银河为介绍西方虐恋概况所编译的《虐恋亚文化》成为许多虐恋者的经典。李银河认为“在西方,虐恋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人群才会去玩的东西,有许多精致的道具。在中国也是这样。” 她在其博客中说:“我倒是觉得那些反对虐恋的人很变态。他们仅仅因为别人有一点跟自己不一样的感觉,仅仅因为自己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就痛骂别人,显得没有教养之极。如果中国这样的人多了,中国只能永远是一个野蛮的国家。而如果喜欢虐恋的人多了,倒不见得有这样的坏处。”
李银河女士的这些“高论”引起了“众怒”,受到“虐恋”反对者的无情地鞭笞和顽强地抵制,甚至是疯狂的漫骂和人身攻击,最后,在其单位领导的出面劝导,李银河决定“封嘴”,用她的话说就是:“少见记者,少说性”。
李银河女士为什么受到围攻和漫骂,李银河女士为什么被迫“封嘴”?有位网民认为:“李银河一直不能系统的阐述她对‘性革命’应该怎样实践的理论,因为她自己对自己现在向公众推介的东西也没多大把握,对于别人提出的一些质疑,她一直都没能正面回答,这样不负责任的学者还是少些为好。”这位网民的话深刻尖锐一针见血击中了要害。李银河女士把虐恋介绍到我国,并认为“虐恋”绝对不是一种疾病,而是一种亚文化现象,是一种很精致、很高雅的行为。不可讳言,正是李银河这种草率研究和不负责任的“推崇”才把虐恋搞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百的“四不象”,斩不断理还乱的“乱麻”,误导了社会道德的性意识,使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人盲目追求,造成不良的“网络风行”,其影响是不容忽略的。
笔者简要系列分析李银河女士在介绍“虐恋”过程中的失误,以便人们准确把握“虐恋”的概念,认清“虐恋”实质,从而正确理解和看待虐恋。
李银河女士失误之处有如下几点:
其一、李银河女士在虐恋翻译上功课做的不到位。
虐恋一词英文为Sadomasochism,是法国施虐作家撒德(Sadism)和受奥地利受虐小说家马索克(Masochism)二者名字的合成词。它的简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SM。由于SM的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是鞭打和捆绑。因此有人又将SM活动简写为 D&B或DBSM。SM是个专有名词。它正确译法应该译为“性虐待游戏”,或“性虐游戏”。
我国,SM早先翻译为“性虐待”,也称性虐待狂,还称性变态。它是一个充满令人厌恶、恶心、不雅的、污名化了的贬义词。其实这是早先人们对SM行为难以界定和非常不理解而造成的误译。这时的SM常常被讽刺为“性虐狂和性被虐狂”,或“性虐待癖和性被虐待癖”。李银河女士提到:“将‘SM’翻译成‘虐恋’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。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,因为它不仅简洁,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: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,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。”这无疑肯定了最早将“SM”翻译成“虐恋”的人是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,但真正使“虐恋”一词,发扬光大家喻户晓的是李银河女士。李银河女士所编译的《虐恋亚文化》是中国有系统的介绍西方虐恋行为的第一本书。它使虐恋一词广为流传。在加上李银河女士对虐恋的“推崇”,使得虐恋成为一时的争论焦点,引起广泛的关注。李银河女士对虐恋的贡献之一就是对虐恋的去污化有一定的作为;贡献之二是加速了虐恋的传播速度。
但在虐恋的翻译上,李银河存在着一定不周和不到位的地方。在中文中的“性虐待”,是个泛泛不确定的概念,如果没有特殊的说明,人们很难搞清楚它是什么性质的性虐待?它更可能理解为虐恋,两者自愿参加的性行为或性活动;它可能被理解为性犯罪性质的性伤害的行为,属于违法犯罪的性侵害和性暴力的范围,如强奸、性骚扰和性暴力等;它也可能被理解为兽奸,一种摧残动物的性行为;它还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摧残性器官的性酷刑,如宫刑、骑木驴等。在英文,以上这些性行为均有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来表达,一词一意,简单明了。性虐待为“sexual abuse”,恋兽癖或兽奸为“bestiality”,性酷刑为“sexual torture”,虐恋为Sadomasochism,简写SM。
我们赞成把“SM”翻译成“虐恋”的做法。如果,李银河在推出“虐恋”的翻译的同时,把英语中真正的“性虐待”词汇“sexual abuse”同时推出,进行比较鉴别,就会减少人们对“虐恋”和”性虐待”的混淆,就会减轻人们对虐恋的误解,从而减少对她本人的误解。在百科全书中,就做得比较好。书中写到:BDSM(虐恋)的实践者认为它和性虐待(sexual abuse)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。
关键字: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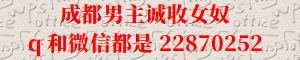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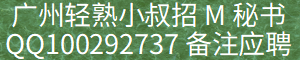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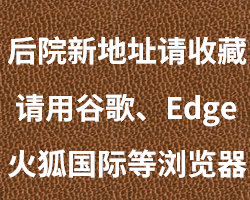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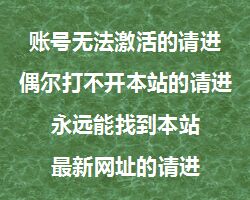
评论